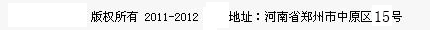上个月,清华附小学生的苏轼研究在朋友圈刷了屏,书单君还为此写了篇文章。
我在文中说,中国教育进入了分层时代,哪怕只是小学,牛校、重点校、普通校的差距已经在变得不可同日而语。
尖端学校的培养水准,想必大家通过清华附小的苏轼研究已经有了感性印象,那么农村、山区等落后区域的基础教育状况,又是什么样子?
本期书单观察栏目的执笔人,是书单团队95后的小伙伴小冒力。前不久,她回到了位于湖南的老家,通过走访学校、书店、亲友,并结合成长经历,对家乡的教育现状有了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。
冒力从小学到初中都在村镇就读。我相信这份生动的记录,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部分农村地区教育发展的水平,以及农村孩子们让人略为忧心的未来。
▼
1
我的家乡是湖南省西部一个普通的乡镇。湘西多山,但家乡的地形属于山地平原,经济算是临近几个乡镇中比较发达的。
爸妈都是初中毕业。我妈年轻时倒是个能写会唱、模样精致的文艺青年,可惜被埋没乡间,没能走上文艺的道路,结婚生娃后,再也没了文艺的心思。
所以,家里没什么藏书,只有《知音》和《婚育》。我的阅读启蒙正是从这两本杂志开始的。
当我还是个刚进青春期没两年的初中女生时,就开始偷偷翻阅爸妈订的杂志了。
《知音》的内容大概就是小姨子和姐夫出轨,谁谁谁得了绝症,又是一场感天动地的人间大爱,《婚育》里面则有很多羞羞羞、啪啪啪的文章。
看腻了这些之后,我开始迷恋当时很流行的《未解之谜》系列。
然而,要买到这书可不容易。因为,离我家最近的书店在邻镇,坐中巴车在坑洼的路上颠簸半个多小时才能到。
就这样,我12岁读《知音》,13岁看《婚育》,14岁读遍了能找到的所有《未解之谜》。
当时,我觉得自己可牛逼了,因为身边的小伙伴们连《未解之谜》都没看过,所以我时不时还会拿里面的知识炫耀炫耀。
后来,我成了镇里为数不多的走出去的孩子,考上了大学,读传媒专业。
由此认识了一些优秀的朋友,他们往往出身城市的中产家庭,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。
当我还在读《知音》的时候,他们可能已经在阅读文青最爱的毛姆,当我连火车都还没坐过的时候,他们可能已经跟父母去过北京、上海甚至东京、巴黎。
尽管这差距时常让我感到自卑,但相比家乡那些十几岁初中毕业去流水线打工,或者在老家开店的同龄人,我还能接触到更大的世界,就已经是值得珍惜的了。
2
我离家求学、工作至今已经将近8年。这8年来,镇上的主街越来越宽,街道旁的店铺越来越多,甚至还有了一家只有过年时生意才红火的KTV。
但唯一不变的,是镇上仍然没有书店。其实,附近十几个乡镇只有一家书店,就是邻镇那家我小时候买过《未解之谜》的“三味书屋”。
这个国庆假期,我又来到书店,发现摆设并没有什么变化。进门最显眼的位置是小孩子用的书包、文具,显然,它们是书店销得最好的商品。
再往里走,是《教材全解》之类的教辅。只在一个书架上,有一些儿童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书,比如季羡林、萧红的作品,与风水、方术、棋谱等大众书籍混放在一起。
▲邻镇“三味书屋”的课外书籍书架
老板谌先生还是跟以前一样,戴着一副金丝眼镜,说话慢条斯理。
他告诉我,像萧红和季羡林的这些书,有时候几个月也卖不出一本,在城里卖得非常火的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和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,在这里几乎没人买。
赶集的时候,有些孩子路过书店,随手翻翻书,看出有点想买的意思,他就跟孩子说:“娃,只要十几块钱,买本看看呗。”旁边的家长赶紧把孩子拉开:“娃,咱别买,十几块钱买本书还不如待会给你买点吃的。”
既然销售这么惨淡,为什么不干脆全部卖教辅,或者只卖书包、文具?
谌先生说:“作为一个书店,应该要有这样的书,万一有人需要,也好告诉他这里有。而且附近这十几个乡镇,也就我这一家书店。生意虽然越来越差,能混口饭吃也就行了。”
不过谌先生告诉我,也不是完全没人买,相比于年长的老师,学校的年轻老师会更注重学生阅读习惯的培养,有些成绩好的学生会听老师的话来买课外书籍。
但我知道,在我们这的乡镇和农村,年轻老师真的并不多见。
3
这次回家,我还去了初中母校镇中学。
学校现在没有一名30岁以下的老师,甚至40岁以下的老师也只有4个。
这与8年前我在镇中读书时相比,情况几乎没有改观。而且,老师们往往身兼数科,教历史的兼着教体育,教数学的兼着教美术。
吴老师今年39岁,是学校的音乐兼计算机课老师。当年,我曾在他的指导下,连续两年夺得县演讲比赛一等奖,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好成绩。
这次来学校才知道,8年过去,我当年的成绩竟依然没有人超越。
吴老师说:“城里的学生越来越厉害,越来越专业了,独舞、乐器演奏那些需要后天培养的项目,我们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,声乐、演讲这些比较依靠天赋的,还能去拿个三等奖(参与奖),表现出色能拿二等奖。城里的教师手头资源多,消息更灵通,所以学生的锻炼机会也比我们多。”
最近,吴老师还给学校开了个